男女主角分别是的美文同人小说《拨乱反正在宋朝》,由网络作家“佚名”所著,讲述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故事,本站纯净无弹窗,精彩内容欢迎阅读!小说详情介绍:一梦醒来,想我堂堂立国一千多年的大周王朝皇室后裔,居然来到了这么一个古怪的朝代,居然大隋之后不是大周,而是唐朝,我大周朝到那里去了,这宋朝虽富,却弱的可以,看我拨乱反正在宋朝,再创我大周盛世!!!!...
《拨乱反正在宋朝》精彩片段
大宋崇宁四年,此时又是一年一度的漕粮进京的日子,那东京汴梁的汴河之上立时比一般的时候更是热闹了许多,这宋朝的漕粮北运之事起源于两汉之时,而后逐渐发展完善,到唐代之时发展到了第一高度,而到如今更是成了那东京汴梁每年最为重要的事情之一,这漕粮最高之时有实征六百万石,用于满足那京城和各方驻军的粮草,可以说这条运输漕粮的汴河,就是这拥有人口百万的当世第一大城,大宋国都东京汴梁的生命线。
而就在这漕粮搬运的码头之外,有一座酒楼,这酒楼占地极大,宽广无比,而且楼层又高,明眼人一看就知这酒楼已经到了那能盖大小的极限,只要再大再高一点就犯了官府的忌讳,就有逾制之罪,这酒楼就是那自太祖开宝元年起,几乎是大宋定都汴梁起就有的如今已经传了有十代,有了一百三十九年,当今汴梁第一,乃至于是大宋第一的酒楼——周家楼。
在这酒楼的顶层天台之上,此时正站立着一人,此人身材壮硕,身高五尺有余,(北宋尺的长短合今尺在30.9~32.9厘米之间,通常为31厘米左右,本书为了计算方便,就再短一点,一尺定为30厘米,后面十寸为一尺,十尺为一丈,后面不再重复解释)周身的肌肉把身上这身宝蓝色的衣衫撑的鼓鼓的,看上去就是一个微矮的壮年汉子,可等到往那人脸上一看,就发现此人面色白皙红润,还带有一丝稚气,头顶既无巾又无帽,更无幞头,这分明是没有行过冠礼的少年。
要知道这冠礼虽是在五胡乱华、五代十国之时曾一时停止,但是自本朝定鼎以来,一些朝中重臣和文人士大夫痛感佛教文化是对大众的强烈冲击,主张要在全社会复兴冠、婚、丧、祭等礼仪,以此弘扬儒家文化传统。本朝那位世称涑水先生。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卒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主持编纂了《资治通鉴》,的司马光司马君实就曾痛心疾首地说道:
“冠礼之废久矣。近世以来,人情尤为轻薄,生子犹饮乳。巳加巾帽,有官者或为之制公服而弄之。过十岁犹总角者盖鲜矣。彼责以四者之行,岂能知之?故往往自幼至长,愚騃如一,由不知成人之道故也。”
他认为废除冠礼,使得人情轻薄,自幼至长不知成人之道,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司马光在其《书仪》中,制订了冠礼的仪式:男子年十二至二十岁,只要父母没有期以上之丧,就可以行冠礼。为了顺应时变,司马光将《仪礼·士冠礼》加以简化,使之易于为大众掌握。此外,还根据当时的生活习俗,将三加之冠作了变通:初加巾,次加帽,三加幞头。
有这名人作为表率,和众多的文人士大夫的提倡,而本朝历来尊崇文事,使得冠礼又重新开始盛行起来,上至王公大臣,下至黎民百姓,更夫走卒,商野小民只要家中有条件的都要在自家孩儿成年之时举行冠礼,就算家中实在贫苦,但也会由宗族安排,统一举行冠礼,不过可能是因为十二岁实在是太小了一些,所以一般举行冠礼的时间安排在一十五岁,如果过了十五岁还没有举行冠礼的那就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家中有丧,无法举行,要么只有一条,非大宋之人。
不过看这少年的穿戴,不像是戴孝之人,又非蛮夷胡种,而且这少年能够来到这周家酒楼的顶层,而且全身不是那伺候人的小厮打扮,分明是一个富家公子的模样,也不是那因家中贫困而无法举行冠礼的人家,那么这么看来,则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这少年天赋异秉,发育的极好,未及成年,身躯就几近成年汉子的模样了。
这少年站在楼顶天台边上,手扶着那四尺八寸高,取上好硬木用榫牟结构拼接,后又用桐油拌生漆涂刷多层,然后在阴干的漆面上以纯铜抽拉成丝,然后在漆面上镶嵌成花纹,然后再有琢玉的细纱打磨的光滑如镜的栏杆上,远看那脚下那汴河码头前,那些脚夫成群结队的从那漕船上搬下一袋袋此次新进入京的漕粮,来到粮食转运之处,从记录的官员手中换取一根根象征着代表一袋粮食酬劳的竹签,然后快速的返回码头,去搬下一袋粮食,用自己的劳力来换取自己的生活所需。
那少年看着脚下好似蚂蚁般忙碌的人群,心中若有所思,这时耳边一阵清脆的铜铃声,这少年听了,仍没有回头,只是静静的看着脚下的一幅众生图,过了片刻之后,那铜铃声已然停止,这时在少年身后那高有两丈宽有一丈深有一丈的,样式古怪,那好像一立起的方砖的房间的木栏形制的大门向两边拉开,从里面走出几个人来。
当头一人身着一袭绸制的青衫,头上一顶湖蓝色的头巾,腭下三缕长须,乌黑油亮,被天台上的大风一吹,那六寸长短的胡须随风而舞,条条分明,根根见肉,此人大概五十来岁,但是保养的极好,肤色红润,额头和眼角的皱纹如果不仔细的观察,恐怕还轻易看不分明。
在这人的身后还跟着两人,都是小厮的打扮,一人手托一个木盘,在木盘之上又各自放着一些东西,有吃食,也有器物,只见那打头那人先让那两个小厮先将手中木盘上的东西,一件件的放在那张开足有两丈方圆,用油布,硬木制成的遮阳伞下的一个矮案上,然后来到那少年身边拱手道:
“禀告大郎!琉璃坊今日又出了一批新的家什,颜色也多了许多,想来离大郎所说的那种透明的水晶琉璃已经不远了,这些新货还请大郎赏玩,还有今日那些按大郎所说,从常州宜兴县掘那些紫砂陶泥,烧成的茶壶已然送到,现以用家中新挖的那口甜水井中的井华水,以银屑炭烧煮之后,已冲泡了自家清炒之法制成的高山云雾茶,和这家中厨子新近制成的几样茶点,请大郎品评一二!”
这被老者称为大郎的少年一听,回过身来,也未说话,就径直来到遮阳伞矮案旁的圈背交椅上坐下,仔细打量起那矮案上的东西来。
只见那少年先用手摸了摸那老者所说的那新制的紫砂茶壶,手指在那茶壶的身上缓缓的滑过,手指感觉到壶身温热,上面的触感既不像景德镇所出的青白瓷那般光滑,也不像陶器般粗糙,近乎与两者之间,与人的肌肤相近,摸起来十分的舒服,整个茶壶有成人巴掌大小,成一梨型,看上去分外的顺眼。
少年一手将茶壶托在手中,又一手提住那壶盖上指肚大小,宝珠形制的盖钮,轻轻一提,居然将装了八分满的茶壶整个提了起来,接着少年一手抓住壶身,一手扭住壶盖左右一用力,听得沙沙的一阵轻响,那壶盖就被提了起来,从而可以知道之前将那茶壶提起来,并不是因为壶盖于壶身之间是卡死的,而是单靠那壶盖于壶身之间由于湿气密封而形成的吸力,由此可见这壶盖与壶身做的轻巧。
那少年的鼻翼微微抽动了一下,吸了一口壶盖掀开后腾起的温热湿润的茶香,又仔细看了看手中的茶壶壶身的厚薄,满意的点了点头,少年将壶盖盖回,将茶壶放到身边的矮案上,然后开口道:
“这壶做的不错,大小正好,壶盖与壶身做的当真是严丝合缝,手艺当真不错,是景德镇的手艺吧?”
这老者一听点点头笑道:
“大郎果然目光如炬,说的不错,正是老奴花大价钱从景德镇挖来的工匠,此人自当年真宗皇帝为景德镇改名起,就在景德镇中制瓷,传了以有数代了,手艺当真是一绝,而且烧瓷也有一手,要不是老奴给他定了大价钱,还统一让他家人徒弟一同聘用,他还不肯来,不过也不亏,要不然这么好的紫砂陶泥,用那些庸人岂不糟蹋了,老奴现今给他定工钱是每月五贯,不知大郎意下如何?”
这少年一听点头道:
“不错,你命人告诉他,他这活干的不错,我赏他二十贯,还有叫他多教几个徒弟,把拿手的本事都拿出来,教的好的话,这个月不算,从下个月起他的月钱是每月十贯!”
那老者一听皱眉道:
“大郎这工钱委实高了些,恐怕不合适吧?(要知道在宋时,一个步入两府的宰相不过月入三百贯,一个普通从八品的县令月入不过十五贯,当然宋代除了本俸之外,还有职钱,禄粟,厨料,薪炭诸物,增给,公用钱,给券,职田等名目繁多的津贴。不过给一个制瓷的一个月开十贯的工钱确实是有些高了。”
这少年一听不以为意道:
“财叔就不要小气了,他的手艺值这个价钱,只要他教出两个有用的徒弟,这本钱就回来了,无须再议,还有这茶壶的身上光秃秃的,也太过单调了一些,不过这可不能像那瓷器一般上面可以挂釉,要不然这紫砂壶的透气的好处就毁了,磁州窑那边剔花的瓷枕,和瓷器却也是一绝,财叔可以再从磁州窑那边再挖几个擅长剔花的高手来,价钱财叔自定即可,到时候让他们在壶身上用剔花之法在上面绘上诗文图画,再入窑烧制,这样这壶身就会更好看一些,不光可以用上剔花之法,就连贴塑什么的也可一并用上,至于具体怎么弄,财叔可自行处理!不用再来问我了!”
那老者听了,边连连称是,边用一只炭笔记在从袖袋中取出的用竹纸钉成的册子上,那少年说完之后,又随手拿起那几件琉璃器物看了看,放回原处之后说道:
“这几件新的琉璃器还不错,不过样式还是单调一些,财叔可以让琉璃坊的人仿照玉器的挂件,配饰制作一些,反正这琉璃又叫药玉,不过颜色上要力求多样,要和那些玉器相比各有特色,此外还可以做些文房器具,和筷托、盘碗之类,不过财叔要记住,这琉璃器的出处一定要处理好,切不可让他们那些外人知道这琉璃器是我们自家产的,要不然后患无穷!”
那老者一听连忙点头道:
“大郎所言极是,不过大郎放心,这些琉璃器是先行运往登州自家私港上船之后,沿那外海转一圈再从泉州港上岸,对外一直是说是那波斯器物,那波斯本就盛产琉璃器当是无人怀疑!”
而后被少年称为财叔的老者看了看守在那进口两旁的那两个小厮道:
“至于家中凡是知道这事情之人,都是当年留下来的老人,和家生子,忠心绝对没有问题,况且他们也都是签了死契的,大郎尽管放心好了!”
少年听财叔这么一解释,这才满意的点点头,接着那少年看了看送来的那几盘吃食,先选了一盘好似酥饼的吃食,随手拿起一块,用手一拿那牛眼大小的酥饼就拿在手中,少年一闻,就闻出一股浓郁的油香,其中还夹杂着一些淡淡的花香。
只见那少年拿这酥饼在手,直接就是放入口中一咬,这酥饼才咬了一口,那少年不禁眉头就微微皱了皱,想那财叔干了多年的管家,察言观色的本事早就炉火纯青,在少年拿起酥饼之后,就一直紧紧的盯着那少年,虽然那少年皱眉的表情一闪即逝,但是还是被财叔看在眼里,忙上前开口道:
“大郎这酥饼是家中厨子,先用油混合上好的面粉,制成酥皮,再包裹上由上年用荷花,桂花和石蜜,加上交趾霜糖腌制成的糖馅,然后上炉烤制而成的,烤好之后表皮起酥,酥脆浓香,内馅甜美异常,家中厨子取名为百花酥,想作为此次家中酒楼新推出来的伴茶点心,怎的不合大郎的口味,不知那里要改的,还请大郎指教!老奴好回去叫他们加以改良!”
被称为大郎的少年,听得财叔这么一问,没有说话,先是又咬了一口,将手中的酥饼吃完,然后将手一伸,那财叔见状赶忙上前,将少年面前矮案上的一叠白纸,抽出来几张交到少年手中,这白纸打开之后,有一张手帕大小,颜色乃是乳白色,纹理细腻,柔若细绸,上面还印有暗花,闻着有一股草木清香之气。
这少年先抽一张把手擦了擦,然后又将嘴唇上的油迹擦干净,接着直接抓过那紫砂茶壶来,也不将茶水倒出,直接嘴对着壶嘴就喝了一大口热茶,幸好这财叔将茶水送上来之前先用热水将茶洗了一道,然后灌入热水,然后还将水倒在自己手上试了试温度,知道正好入口,这才送了过来,而这紫砂茶壶保温极佳,虽然放了一段时间但却没有降下多少温度,正好不冷不热,要不然这少年可要遭罪了。
那少年将一口热茶灌下肚去这才好过一些,又抽了张白纸将嘴角的茶水擦干净,随手将茶壶和那用过的白纸放回矮案上,这才开口问道:
“这酥饼的酥皮是用什么油和的?”
那财叔一听忙回答道:
“回大郎,这酥皮是用牛油和的,怎么不对么?”
这少年一听点头道:
“用牛油的话成本委实高了些,再说本朝一向爱护耕牛,这牛肉牛油本就数量稀少,虽然自家的庄子之中,还有牛养,在江南那边水牛也多,不过这样还是不便大量提供,这样,将这酥饼分为两等,一等用牛油和面,二等用豚油和面,那豚长的快,生的多,体内油脂又多,应该可以将成本降下来!”
财叔一听少年要将这豚油和面,面露异色,连忙劝解道:
“大郎,这用豚油和面恐怕不太好吧!那些能来喝茶的大多是一些文人雅士高门大户,如用豚油,恐怕他们会不喜欢吧!到时可就不太好了!”
少年一听这财叔的疑虑,不已为意,笑着摆摆受道:
“这可无妨,财叔多虑了,想我将这周家酒楼重新开业以来以有四年时间了,推出了多少新菜,全是以前人不吃的,那豚肉、泥鳅、甲鱼,那道新菜推出,这些文人雅士高门大户都赶着上门来品评,连诗文都写了不知道多少,如今人们已经不在忌讳吃豚肉了,财叔你看这几年这集市上豚肉涨了多少价钱,那些文人雅士高门大户就算自己不道集市上去买豚肉,也大多开始自己私下养豚,自家杀豚取肉,所以用这豚油没有问题,况且还有另一种牛油的,只要提前说明即可,不过这酥饼的馅心委实甜腻了些,不适宜和这清茶同用,不过财叔回头你让厨子将这酥饼的味道调淡一些,配着那煮茶发煮出的茶水,却是正好,对了财叔这花瓣的馅心制作可麻烦,可以保存多久?”
财叔听少年这么一问,闭目思量了一会,这才回答道:
“回禀大郎这花瓣的馅心倒是很好弄。将新鲜采集下来的花瓣用流水冲净浮尘,然后有细纱布拧干水分,挤去其中的苦汁,然后取一新成瓷坛将起清洗干净,阴干,然后将花瓣与霜糖层层铺入,一层花瓣,一层霜糖,层层铺紧,压实,直至坛口,然后倒入上好的蜂蜜,将整个瓷坛装满,然后盖上坛盖,用蜂蜡胶泥风口,然后装入细布袋中,埋入一丈深的地下,将土盖实,三月后取出即好,以后只要封的严实,放入冰窖当中,最少可保存三年以上,不知道大郎问这有何事?”
少年一听点头道:
“既然如此好制,而且保存时间如此之长那就好办了,财叔你是知道的,本朝盛行那十二花神,财叔可命人按月采集那正月梅花二月杏花、三月桃花、四月牡丹、五月石榴、六月莲花、七月蜀葵、八月桂花、九月菊花、十月木芙蓉、十一月山茶、腊月水仙的这十二种花瓣,一年以后可每月提供当月花神花瓣制成的酥饼,也可一次将十二种酥饼一并摆出,十二种每种一枚,拼做一盘,就取名花神酥,到时候那些自誉风流雅士之人定争相购买,到时候定有赚头,财叔你价钱不用定的太便宜了,牛油的每盘一贯,豚油的每盘七百文,那些名士可不管价钱,越是贵的,他们买的越欢,财叔可不要手下留情啊!”
财叔听得少年嬉笑的话语也笑道:
“大郎说得是,他们这些人就是越贵越买,到时候老奴再让他们按照花朵的模样制成各色的模子,到时候酥饼做得和花朵差不多,他们一定喜欢,大郎你再尝尝其他几样吃食,这也是新作的,也请大郎品评、品评,也好让他们那些不过做了一两道新菜就自吹自擂的厨子知道什么叫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少年一听也是摇头一笑,看了看另外几样吃食,都成方糕的模样,四四方方的,有米白色的,有表面光滑,青绿色的,还有完全透明混合有一粒粒各色小方块的,少年看见这几样吃食的模样,很是喜欢,就每样吃了一块,那米白色的香糯可口,里面还有芝麻的糖馅,那半透明青绿色的爽滑弹牙,清香爽口,这透明的,口感与那青绿色的差不多,但是充满了果香,里面那一粒粒的都是各色的时令水果,吃起来十分的爽口,这少年吃着十分的舒服,于是每样又吃了一块,脸上也露出了一丝笑意。
财叔见少年吃的高兴,连忙在一旁解释道:
“大郎,那米白色的乃是用上好的糯米打磨成粉,然后包裹甜馅蒸出来的,共有两种内馅,一种是芝麻糖馅,一种是赤豆沙馅的,那青绿色的是按大郎要求用绿豆打磨成精粉,然后与水相和,加入各种滋味后,蒸熟既成,这是鲜甜口的,还有一种酸辣口的,不适合与茶同食,不过也别有一番滋味,至于那透明的,是照大郎的吩咐,从登州海边捞来海花菜,熬煮出精华,然后过滤冷却后结成透明无味的琼脂,然后再将这琼脂按照比例加入那清水之中,然后再次煮沸,接着加入新压榨的果汁还有石蜜,以及霜糖,接着在在其中加入切成半个指肚大小的时令水果的果肉,接着混合均匀,倒入模具当中,接着让其自然放凉,用冰块降温也可,待其重新凝结之后,这就成了,不知大郎觉得这几样可好?”
这少年一听点点头道:
“这几样都做得不错不用改了,可以直接上家里酒楼的单子,不过这糯米粉、绿豆粉、还有琼脂的作用不指这些,让家里的厨子们好好琢磨琢磨,不过那琼脂我倒想出一道新吃食,财叔等会儿你下楼之后,命那些厨子们取鸡子五枚,从大头出取下一块蛋壳,然后从中将蛋液倒出,用于厨房其他菜式,要保持鸡蛋壳的完整,接着再熬煮一锅琼脂,分成五份,然后分别混入酸、甜、苦、辣、鲜五种滋味的汤水,酸的可用杨梅熬汁,混入杨梅肉丁,甜的可以用霜糖、蜂蜜熬煮,混入水果丁,苦的可以用茶叶熬煮,混入抄水的胡瓜丁,辣的则用花椒熬煮加入蒜末,鲜的则可用鸡肉豚骨熬成高汤,加入抄水的香菇丁,或已经制熟的鲜虾粒,或已经熟了的肉末,或是鸡丝,将这五种混合了不同味道的琼脂分别倒入那五个鸡蛋壳中,然后再原样封好,等琼脂完全凝结之后,就五枚一组,一起上,取名就叫五味俱全,这蛋壳上没有标志,那一枚是什么味道,谁也不知道,到时候让那些吃客连猜带吃,一定卖的好,到时候一份五味俱全就卖他三百文一定好卖!”
那财叔一听忙将少年所说的记到手中的册子上,点头道:
“还是大郎本事高,这么一会就想出一道新吃食,等会老奴就叫他们去试试,不过讲到这老奴却想起两个人来,想来可以满足大郎对于那紫砂壶上题字刻画的要求!”
这少年一听,眉毛一挑道:
“欧!财叔说得是那两个人,当真那么厉害么?”
那财叔将身子一挺,扬声道:
“回禀大郎得知,正是有两个人有此本事,不过这两人犯了事,正在开封府大牢里押着呢!这两人一人姓萧名让,乃济州人,秀才出身,会写诸家字体,尤其擅长苏、黄、米、蔡四种字体,擅长模仿历代名家字体,足可乱真,亦会使枪弄棒,舞剑抡刀,在江湖上有一个日诨号叫做圣手书生,另一人名叫金大坚,乃本朝有名的金石雕刻家,善刻苏、黄、米、蔡四种字体。技法纯熟,雕刻栩栩如生,那金大坚开得好石碑文,剔得好图书、玉石、印记,被称做玉臂匠。想来凭他二人的本事,一定可以达到大郎的要求!”
少年一听奇道:
“那二人如果有这般本事,怎么会沦落到开封府大牢中去呢?”
那财叔摇头笑道:
“大郎有所不知了,这二人也是倒霉,当日也不知是那一方的强人因为自己的大当家被抓,想要救人,但县府大牢的守备森严,无法下手,就出了一个主意,那强人中的另一首领的命人将那萧让、和那金大坚连同他们的家人一同抓了过来,以家人的性命为要挟,强迫这萧让、和那金大坚二人,一人伪造了开封府尹的亲笔书信,一人伪造了开封府的官府印信,制成一封伪令,还有一封大理寺文书,说这强人的大当家的在开封府境内,也犯有案件,要将人犯押往开封府,那抓住强人的不过一上等小县,怎会怀疑那文书有假,赶忙安排人手和那强人伪装的衙役,押送要犯前往开封府,半路之上,那些强人暴起,劫了囚车,抢了人犯,杀了押运的衙役,扬长而去,那小县县令得知之后,忙向上面奏抱,这才知道文书有假,那开封府尹大为震怒,追查下来,可是那些强人早就跑了一个干净,没有办法只好把怒火对准了那伪造文书的萧让、和那金大坚二人身上,这二人刚连同家人被强人放回,人还没有回过神来,就又被抓进了开封府大牢,本来开封府尹在查明事实之后,念在他二人为贼人所迫,伪造文书乃是无奈之举,也就将二人轻判了,本来伪造官府文书至少是个刺配的罪过,但是开封府尹却判了他二人罚银抵罪,可是这二人的家财早就被那伙胁迫自己的强人卷了一个干净,自家生计都成了问题,连房子都被强人烧了,这俩人只有乖乖的在开封府大牢里吃牢饭了,至于大郎要问老奴如何知道的这么清楚,那是因为前些日子家中又招了一批人,其中就有这二人的家人,老奴在打探这批新人底细的时候,顺便打听出来的,不知大郎觉得这二人可用否?”
那少年一听,点头道:
“既然是财叔打听过了,想来不会有错,财叔尽管花钱将那二人赎出来就是了,不过到时候再跟他们两个签上一份死契,这样就完无一失了,还有到时候,他们两人的其他家人也一并收拢过来,这样这二人才好安心!”
财叔一听点头道:
“大郎所言甚是,等会老奴就去办,对了前些日子,有一个叫陶宗旺的前来投靠,此人乃光州人氏,庄家田户出身,两臂有千斤之力,习惯使一把铁锹,也能使枪抡刀,人唤“九尾龟”。打理庄稼是一把好手,而且挖渠,造房的手艺也是不凡,老奴就安排他在城外田庄中专伺打理庄稼和挖渠,造房之事,不知大郎意下如何?”
那少年听了笑道:
“此等小事,财叔何须来问我,财叔自己处理便可,这些年来财叔办事我还是放心的!”
那财叔听少年这么一夸,连忙笑着摆手道:
“大郎过于赞誉了,老奴只是紧守本分而已。前日王升王老武师推荐一个叫汤隆的铁匠来咱家的铁器坊,不知大郎可要见上一见?”
大郎听财叔说自己的铁器坊又来了一个新的铁匠,还是那王升推荐的,就有了一丝兴趣,不过一个新来之人,还没有显露什么本事,作为那主家的当家,就眼巴巴的跑去见他,未免有些露怯,想到这里,那少年沉思一会,觉得因该再问问清楚,再做决断,想到这里,这少年开口道:
“见我就暂时先不见了,那王升是京中有名的武师,枪棒之术乃是一绝,他儿子王进也入了殿帅府,据说过不了几年就可以当上禁军的教头了,想来以王武师的见识应该不会推荐一个庸手过来,而且财叔你做事一向谨慎,就算是熟人推荐也会调查一番再收下,况且铁器坊是一个紧要之处,万有错处,那就大事不好。想来财叔以将这汤隆的本事底细,财叔已经调查清楚了,还请细细讲来吧!”
财叔听少年这么一问,忙笑着回答道:
“大郎这些年可将老奴看了一个通透,老奴干什么事都瞒不了大郎,老奴听王武师推荐之后,就布下人手将那汤隆调查了一个通透,知其本事才敢将他引入铁器坊来,回禀大郎,这汤隆的父亲原是延安府知府官,因为打铁,遭际在那西北种谔帐前叙用。年前因其父亲在任上亡故,可这汤隆贪赌,其父亲又占了多年的铁器之利,得罪了不少人,所以其父死后,汤隆被人设计,赔光了家产,丢了差事,所以流落在江湖上,无钱就打铁度日。因整天锻造军器,火器飞溅,以致全身伤疤,又好使枪棒,所以人称“金钱豹子”。此人善使一柄三十斤重的铁瓜锤,很是有几分本事,近日因来东京投亲,这才被王老武师推荐过来!”
那少年一听点头道:
“既然其父能在老种经略相公处得意多年,想来也是一个有本事的,西北之地历来战事不休,兵器如果差一些,恐怕就落不得好了,想来他汤家的手艺是不错的,那汤隆祖传的手艺想来也是不差,要不然也对不起那金钱豹子的名号,不过财叔要告诉他自进我周家门之后那赌之一字就要少沾了,虽说小赌宜情,大赌才伤身,但是我家却是不许了,财叔你要好好的告诉与他,如果不能戒去滥赌的嗜好,我周家的大门就不用进了!”
这财叔一听连忙点头道:
“那是那是,这个老奴也是知道的,不过大郎放心,自从这汤隆吃了这一场大亏之后,这赌却是碰也不碰了,就算现在咱家推出的斗球赌赛,这汤隆也就是只去看,赌却沾也不沾了,大郎放心就好!”
那少年一听点点头道:
“这样就好,对了那汤隆来东京投亲,投的是那一门亲戚,如果也是铁匠出身的话,如果能和汤隆家做亲戚的话,想来也是有几分手艺的,正好那铁器坊中缺人,就叫他家亲戚一起过来帮忙便是,财叔你回去之后,告诉那汤隆,只要是有本事的我周家都收,工钱好说!”
财叔听少年这么一说,却赤的一声笑了出来,见少年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的模样,连忙解释道:
“大郎,汤隆他们家亲戚咱家可请不起,说来这人家大郎你也认识,就是那历代供奉官家,世代皆为朝廷金枪班教头的金枪徐家!”
少年一听眉头就是一挑,哦了声之后,问道:
“原来是金枪徐家,这金枪徐家的枪法天下少有,最近顶了其父金枪班教头的金枪手徐宁,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功夫远超乃父,号称天下独步,当年那徐家先祖随大军北战辽国之时,夺得一套辽国大将的雁翎圈金甲又称“赛唐猊”,乃是当年唐朝宫廷旧藏,据说可以媲美那三国吕布吕奉先的兽头吞天连环铠,是难得一见的宝物,我都没有见过据说已经传了四代了,当日朝廷王太尉要出三万贯索买,那徐家也没有出手,当真是宝物,不过这金枪手徐宁怎么和金钱豹子汤隆成了亲戚了?”
那财叔一听少年发问,连忙在一旁解释道:
“大郎有所不知,说起来这徐、汤两家颇有渊源,想这徐家有两套家传本事并称于世,一为金枪班的金枪枪法,还有一为专破北方连环甲马的钩镰枪法,而这钩镰枪的枪样就是汤家祖传的,那徐家之人就是靠着这钩镰枪破了辽国军马,才夺得了那雁翎圈金甲,至此徐、汤两家开始互有联络,自徐宁祖父时,那徐宁祖父也是一代天才,居然将两套祖传的金枪枪法和钩镰枪法合二为一,创出集两家所长的黄金钩镰枪枪法,为徐家决不外传的秘传之术,而汤隆的祖父则更是用心用力,按照徐宁祖父的要求,和自己的设计,打造出一杆丈二黄金钩镰枪,为徐家专用兵刃,后汤隆的祖父就将自己一女嫁入徐家,就是徐宁的母亲,也就是汤隆的姑姑,所以那汤隆与徐宁是亲表兄弟。”
这少年听财叔这么一说,点点头道:
“原来这汤、徐两家原来有此渊源,那回头财叔叫汤隆打几样自己拿手的兵器,送过来瞧一瞧,我要看看他的本事,现在我已经筑基有所小乘,那三个弟弟也快摸到筑基的门槛了,是时候准备打造兵器的材料了,先准备几年,然后开始打造,如果那汤隆本事可以,就让他来插把手,想过个四五年,等我兄弟的身子完全长成之后,兵器就可以打造完成了,正好使用,对了财叔,老二和老三要修复相貌的药材准备的怎么样了,当年母亲去世之前,就是牵挂他们两人的相貌,深感对不起他们两个!”
少年说着,脸上就露出一丝哀意,而那财叔听罢,也沉声道:
“大郎别怪老奴多说一句,看二朗和三郎的模样恐怕是好不了了,那京城的几大名医都看过了,说是当年那用药正常的后遗症,是已然无法改了,要不然那二郎、三郎的命早就没了,再说那二郎、三郎现在长的并不难看,只是相貌有些奇异而已,二郎、三郎自己也不觉的难看,而且是药三分毒,吃多了总是不好,现在二郎、三郎、连同四郎一起随着大郎炼气多年,身体都是康健壮硕,又何苦没事吃那苦药汤子呢?现在二郎、三郎吃那药汤子已经吃得厌了,又何苦逼他们呢?”
那少年听了财叔的这么一番劝解,点了点头道:
“财叔说的我那里不知道,可是这毕竟是母亲的遗愿不是,罢了,既然老二和老三他们不想吃,那吃完这最新的两帖药后,再不见好,就让他们两个不要吃了,财叔说的也对,是药三分毒,虽然都是一些固本培源,乌发养肤的上佳好药,但是没病吃药,吃多了总是不好,就让他们两个停了吧,对了那师师和念奴那两个丫头怎么样了,在府中还习惯吧!”
财叔听得那少年突然问起前几日,自家的大少爷到矾楼和矾楼大东家正准备商议两家联合的事情的时候,正好碰见矾楼里面的老鸨正在调教两个新买的丫头,那自家少爷见两个丫头哭的可怜,一时心软,就向矾楼大东家说要买这两个丫头,那矾楼的大东家正为与周家酒楼达成联合的事高兴,立刻二话没说,也没有要自家少爷的银钱,就直接将那两个丫头的卖身契送了过来,还一人送了一身好衣服,回来之后少爷没有在意,但自己一看,不得不佩服自家少爷的眼光毒辣,开始在矾楼的时候,在灯光之下看不分明,而且两个丫头都满脸鼻涕眼泪的,看不处是美是丑,现在回府之后,一梳洗干净,活脱是两个大美坯子,要不是被自家少爷掏了过来,恐怕不出五年,矾楼就要多出两个名漫天下的头牌来。
今日看见少爷突然这么一问,那财叔心中感叹,自家的大郎终于是大了,终于知道这男女之事了,想到这里,那财叔嘴角微翘,露出一丝诡异的微笑,然后恭恭敬敬的回答道:
“还请大郎放心,那两个丫头现在正在被喻嬷嬷带着教导府中的规矩,等过几天喻嬷嬷觉得可以了,就让她们两来伺候大郎的起居,大郎是该要两个贴身丫头了。”
那少年没有听出财叔口中贴身丫头的寓意,也觉得自己现在的事物越来越多,是该要两个贴身亲近的帮自己处理事物,照顾起居了,那两个签了卖身死契的丫头,正好,于是随口就答道:
“喻嬷嬷是当年从宫里出来的,有她管教因该错不了,有她在,那内宅之中我也就放心了,对了财叔你还有什么事么?没有的话,就回去歇着吧,不用陪我在这浪费时间了!”
那财叔一听少年这么一说,连忙说道:
“大郎说笑了,老奴现在那有闲心歇息,自从大郎五年前起,执掌咱家这酒楼,不过区区五年的光景就将当年不过在东京诸多酒楼当中实属中等的酒楼打理成现在这副光景,如今已然成了酒楼当中的魁首,在汴梁七十二楼当中当属一流,能和咱家比的只有那美女如云的矾楼了,如今咱家又合矾楼联手,现在这七十二楼当中又有谁是咱家的敌手,如今这东京汴梁之中,那些当官的,如果没有在咱家酒楼吃过一顿的,都不好意思在别人面前说自己是京官,那漕粮没有进京之前,酒楼生意大多清闲,而现在漕粮入东京,咱家酒楼是看那汴河的绝佳去处,天天忙的歇不了板,老奴那里能休息的下来,还有那些定了会员的达官贵人,都要来续签会费,正是忙的时候,照实是不能歇了,大郎就不要再说什么歇不歇的了!”
少年一听,点点头道:
“是啊!又要到最麻烦的时候了,那就要麻烦财叔多辛苦了,不过那会员的名册到时候,照旧送到我这里过目一遍,还有那膳食备载要实时更新替换,以及那新近入京官员的喜好,也要调查清楚,这才是我周家酒楼立足东京的根本,这东西可马虎不得,财叔可要切记,切记啊!”
财叔一听连连点头道:
“大郎所说甚是,这却是马虎不得,不过大郎你今年已经实岁一十有五了,虽然咱周家如今以只剩下你家一支独脉,但是这冠礼还是要行的,家中虽然已经上无长者,冠礼之仪可以从简,但大郎你至少要有一个表字吧!虽说咱家没有什么相熟的文士大儒,大郎您的开蒙恩师,一年前也去了,未曾给你留下一个表字,不过老奴也打听过,如果这样,其实表字也可以自己取的,大郎你自幼聪慧看的书也多,就自己起一个吧!还有二郎、三郎、四郎,你的三个弟弟,如今老爷、夫人都以不在,俗话说得好,长兄如父,你那三个弟弟的冠礼也就是这两几年了,这表字也要你来取,还有小四,由于最小,老爷就一直没有取名字,现在他都已经十一了,总不能周小四这么叫着吧,再说也不好听啊!知道的是叫周家的四少爷,不知道还以为叫周家的小厮呢!大郎这你可要想个好名字!”
这少年一听财叔这么一说,也幽幽的叹了一口气道:
“是啊!没有想到一晃之间已经过了怎么多年了,父亲已经去了五年多了,母亲也去陪伴父亲三年有余了,我的表字倒是好说,不过二郎、三郎、四郎的表字以及四郎的名字倒是要仔细思量一番,我周家依旧实行那汉时,单字为贵,的取名执之法,到我这一代依家谱所定,当是取那字中有宝盖头的单字,我生于元祐六年,据母亲告诉我名字的来历时说的是,当时天降大雨,我出生之时顿时风停雨息,当时父亲在产房之外,听得我出生的消息,正好屋檐有几滴雨水滴在父亲脸上,于是父亲就给我取名为宇,宇字寓意一为屋檐,一者是上下四方,就是说好男儿要志在四方,想那《张衡·东京赋》中有德?天覆之句,那?通宇,那么我的表字就叫德天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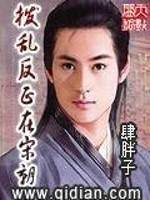

最新评论